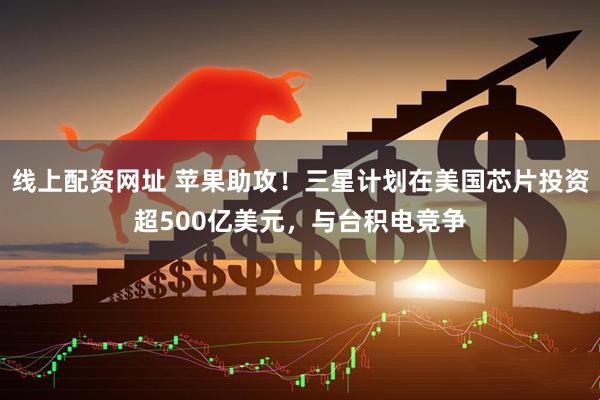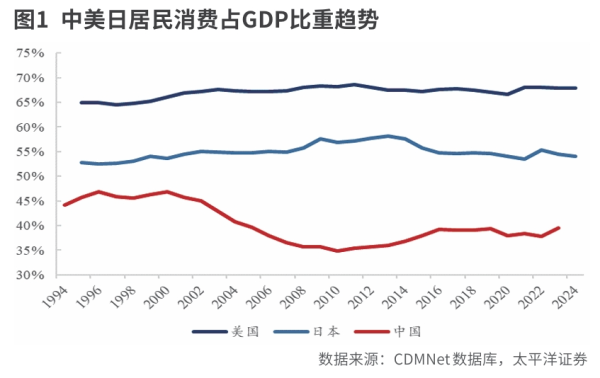我那篇谈《家》的短文发表以后,有些读者来信要我继续就谈《春)和《秋》,我的小说都是失败之作,我的创作经验更不值得多谈。读者们关心小说中几个人物的命运股票配资平台股票,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他们的事情。有些热心的读者甚至希望那些书中人物全是真实的人,而且一直活在读者中间,跟读者们共同呼吸新中国的健康空气,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不忍辜负这些读者的好心,便要求《收获》编辑部的同志们允许我占用杂志的儿页篇幅,谈一些我自己差不多已经忘记了的琐碎事情。
我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写过一篇《爱情三部曲的总序》,在那篇长序的最后,我引用了“一个青年读者”的来信。我接着说:“这个‘青年读者’不但没有告诉我她的姓名,她甚至不曾写下通信地址,使我无法回信。她要我写‘一篇新的文章来答复’她。事实上这样的文章我已经计划过了,这是一本以一个女子为主人公的‘家’,写一个女子怎样经过自杀、逃亡……种种方法,终于获得求知识与自由的权利,而离开了她的专制腐败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三年后(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第一次修改《爱情三部曲》,在这一段文章的后面加了一个小注:“这就是最近出版的《春》,因为《春》刚刚在三四个月以前出版。
我当初计划写的那本小说并不是《春》。淑英的故事是虚构的,连淑英这个人也是虚构的。我所说的“真实的故事”是我在日本从一个四川女学生的嘴里听来的。这位四川姑娘有一次对我谈起她自己出川求学的经过,她怎样跟她父亲进行斗争。她自杀未遂,逃亡又被找回家,最后她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又得到哥哥的帮助,顺利地离开了家乡。她的话非常生动,而且有感情。我说我要把她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她并不反对。可是不久我就动身回国,在上海忙着别的事情,连这个长篇的计划也搁起来了。
展开剩余92%一九三六年《文学月刊》在上海创刊,由我和靳以主编。其实是靳以一个人在负贵,我不过在旁边呐喊助威。刚刚在北平编过大型刊物《文学季刊》,气魄很大,一开目录就是三个长篇连载:曹禺的四幕剧《日出》,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第三个题目他派定我担任。那个时候,我的小说《萌芽》被禁止发卖,《电》虽然出版,却被国民党的审查老爷们删得七零八落,而且良友图书公司为了我这本书和几本别人著作的顺利出版,曾经花过几百元稿费买下某一位审查老爷的一部不能用的大作。我一方面不愿意给新的刊物招来麻烦,另一方面又要认真地完成新刊物交给我的任务。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四川姑娘的故事,我也想到了《春》这个题目。接着我又想到了《家》的续篇。于是我找到了“淑英”这个人物。轮到我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把四川姑娘的故事改成了淑英的故事。一个在花园里长大的深闺小姐总不是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人物吧。我想用她来骗过审查老爷的眼晴。我不仅写了淑英的故事,我还创造了另一个少女蕙的故事。但是刊物出到第七期,终于同其它十二种刊物同时被禁止了。没有什么理由,反正审查老爷看不顺眼。我的小说
只发表了十章。其实我就只写了那么多。刊物按期出版的时候,我每个月至少总要写一万多字。刊物一停,没有人催稿, 我也不再写下去。这时我又忙着做丛书编辑的工作,也写一点别的文章。后来稍有空闲,我翻出发表过的那十章旧稿,信笔增删了一些,高兴时接下去写一点,有时写得较多,有时写得少。小说还没有写完,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抗日战争暴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印小册子。后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租界当局改变态度,朋友们相继离去。我也曾有意离开上海,又知道不能把《春》的原稿带在身边,想来想去,终于抽出十几天的时间,日也写,夜也写,把小说告了一个小段落,作为第一部,交给开明书店。我心想短时期内不会续写第二部了。
倘使我当时真的走出了被称为“孤岛”的上海,《春》的第二部也许就不会完成了。可是我终于没有走。开明书店也准备在上海排印、出版这本书。我便重新拿起放下的笔,将淑英同蕙这两个少女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那些日子的确不是容易度过的。正如我在《春》的《序》上所说,我好几次丢开笔,想走,好几次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写不出一个字,好几次我几乎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但是我终于写完了《春》,写下了“春天是我们的”这句话。我觉得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
这些力量是成干成万的青年给我的。在那个时候不断我鼓舞、使我能够支持下去的,是千万青年的纯洁心灵,是我对青年们的爱。那个时候我除了写作外常常在霞飞路(现在滩海中路)上散步,我喜欢看那些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每
次看见青年学生抱着书从新开办的学校和从别处迁来的学校里走出来,我就想到为他们写点东西。回到自已的房间拿起笔写小说,我就看见平日在人行道上见到的那些天真、纯洁的脸庞,我觉得能够带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和希望是我最大的幸福。
写完了《春》,看完了全书的校样,我就坐上海船经过,
香港到广州去了。我在《序》上写着:“我一定是怀着离愁而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着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我关心他们,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却愿意将这本书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献给他们”。
我在这里用了“不配”两个字,并非谦虚。我甚至在今天还珍惜我这点真诚的感情。倘使我的作品果真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一点点温暖和希望,那么我这一生便不是白活了。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的好的东西,这才是作家的光荣。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愿意我能够做到。
在《春》的扉页的背面我预告了《秋》。我开始写《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写《秋》,正如我开始写《家》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写《春》。
《春》和《家》一样都是匆匆地结束的。《春》是《家》的补充,《秋》又是《春》的补充。
三本书合在一起便是一本叫做《激流》的大书:《家》在《时报》(一九三一年)上面发表的时候用的就是激流这个名字。
我在《时报》上发表长篇连载完全是意外的事情。我并不认识《时报》的编者。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敌,他忽然托一位我在世界语学会常常遇见的朋友来找我商量,要我替《时报》写一部长篇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惑谢朋友推荐的好意(可能是由于他的推荐)就答应了编者的要求。我写了《总序》和小说的前二章交给那位朋友转送报馆。编者同意先发表它们。以后我每隔一星期的光景送一次稿到报馆,随写随送。(小说的每一章原来都有小标题:第一章是《两兄弟》;第二章是《琴》。开明书店的单行本也保留了它们。一九三七年《家》改排新五号字本的时候,我才把它们删去。但是这个本子刚印好就被“八·一三”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以后重排的新版本里也就没有了小标题。)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上艰苦作战,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参加救亡运动。我和别人一样,也“动”了一个时候。《时报》上发表小说的地位也被更重要的东北消息占去了。但是那些时候国民党政府不仅一味退让,而且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人民的爱国运动。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气势越来越高。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经常在虹口演习作战,威胁当时所谓“华界”的安全。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离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厂不远),有时候一天中间谣言四起,居民携儿带女搬进租界,不到一个月功夫弄堂里的住户竟然迁走了一小半。住在我楼上的朋友全家也搬进租界去了。我一人住房一所二层楼房,石库门里非常清静。白天我不常在家,晚上回来,我受不了那样的静寂,对着一张方桌和一盛弧灯,我又翻出来几个月的小说剪报,重新拿起我那支自来水笔,接着一两月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我写得很快,也写得匆心。哪怕我这两扇石库门内静得象一座古庙,我也不能够从容落笔。日本的兵营就在这附近。静夜里海军陆战队很可能来一个“奇袭”。我也不能不作万一的准备。所以我决定早结束我的小说。
那个时候《时报》也换了编辑,原来的那一位编者请假回乡去了。我的小说停刊一个时期之后,时报馆忽然写来一封信,抱怨我的小说太长,说是比原先讲定的字数多了许多。他们并没有明白地拒绝续登我的小说,但好象有这样的暗示。这样的信自然不会使我高兴。不过我也不想跟时报馆打官司。好在我的小说也可以收场了。过了几天我写完《家》的最后一章,我就把剩下的好几万字原稿送到《时报》馆,还附去一封信,向编辑先生道歉:我的小说字数超过了他们的需要。我说他们不登续稿,我无意见。现在送上这批原稿请他们过目。倘使他们愿意继续刊登,我可以放弃稿酬。结果我的小说终于在《时报》上全部刊完了。不用说,报馆省掉了几万字的稿费。他们的做法并不是公道的。但是我总算尽了我做作家的责任。我不是为稿费写作,我是为读者写作的。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这样地结束了。这时候我才想到《家》和《春》这两个书名。我结束的是《家》,不是《激流》。《家》并没有把我所要写的东西全包括在内,我后来才有写《春》的可能。《春》固然写完了蕙和淑英的故事,但是还漏掉了高家的许多事情,我并没有写到“树倒猢狲散”的场面。觉新的故事也需要告一个小段落。因此我在结束《春》的时候,就想到再写一部《秋》。我并非卖弄技巧,我不过想用辛勤的劳动来弥补自己作品的漏洞。
我唠唠叨叨地叙述这些琐碎事情,无非说明: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曾写出完整的作品。我的几部小说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也并非苦心构思的结果。一些偶然的事情对我的作品的面目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我认为艺术应当为政治服务,我一直把我们的笔当作攻击旧社会、旧制度的武器来使用。倘使不是为了向不合理的制度进攻,我绝不会写小说。倘使我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不曾身受过旧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不曾目睹人吃人的惨剧,倘使我对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并不深恶痛恨,对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并无热爱,那么我绝不会写《家》、《春》、《秋》那样的书。我曾经多次声明,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拿起笔来写小说。倘使小说不能作为我作战的武器,我何必花那么多的功夫转弯抹角、钮怩作态、供人们欣尝来换取作家的头衔?我能够花那么多的笔墨描写觉新这个人物,并非我掌握了一种描写人物的技巧和秘诀。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的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制度。
我想借这些话来说明我的创作方法,来说明我怎样写《激流三部曲》,让读者知道我的浅薄和我的作品的缺点。有人不了解我为什么要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实一句话就以说得明白:我不断地发见了它们的缺点。我去年又把《家》修改一次。最近我改完了《春》,补写了婉儿会到高家给太太拜寿的一章。补写的一章更清楚地说明冯乐山究竟十怎样的人。在这一点曹禺改编的剧本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提到了冯乐山打骂婉儿的事,不用说,这是看了曹禺的戏以后才想到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心目中的冯东山并不完全一样。
曹禺写的是他见过的“冯乐山”,我写的是我见过的“冯乐山”。我见过的那个冯乐山高兴起来也会把婉儿当成宝贝一样。他害怕他的太太,因为他的太太知道他欺负孤儿寡妇的丑事。我还把《春》的第一部同第二部合并成一部。我从前觉得把小说分成两部好,现在却认为合并成一部也未尝不可。这说明一则我手中并无秘诀,二则象分章,分卷这些小节与一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并无多大关系,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面记错了人物的年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面也有把时间弄错的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两部伟大的作品也并不曾因此减色。我既使在这些小节上花了很多功夫,也不能使我的几部作品成为杰作。一部作品的主要东西在于它的思想内容,在于作者对生活对社会了解的深度,在于作品反映时代的深度等等。
现在我又回到《春》上面来。应当首先提到的人是淑英和蕙。这两个少女性格相似而结局不同。环境决定了她们的命运。蕙被人虐待痛苦地死去,淑英得到堂哥哥们的帮助逃出了囚笼。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也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凭空创造。我在我的姐姐妹妹和表姊妹们的身上看到过她们的影子,我东拼西凑地把影子改变成活人。我写蕙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我死去的三姐。我离开成都的前一个月参加了三姐的婚礼。三姐上轿的情形就跟我在小说中描写的蕙的出嫁差不多,不过三姐心目中并没有一位表哥,而且她出嫁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几岁,只能做人家的填房妻子。不知道么缘故,她上轿时挣扎得很厉害,看见的人都有点心酸。在那个时代男人娶妻、女子出嫁都好象抓彩一样,尤其是从来脚不出户的少女,去到一个陌生人家,一切都得听别人支配
,是好是坏,全碰运气,自已作不了一点主。旧式女子上花轿的痛哭不是没有原因的。据说三姐相当满意她的丈夫。三姐夫并不是郑国光那样的人,然而他的父母却很象郑国光的父母。我根据三姐的病和死写了蕙的病和死,连觉新写给觉慧报告蕙的死讯的信也是从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信中摘录下来的,觉新所说“三叔代兄拟挽联一副”也是我的二叔替大哥拟的挽联。觉民想的一副对联:“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其实是我的六叔想出来的。他在来信中提到这八个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信早已遗失,可是这八个字到现在我还记得。三姐去世的时候,我同三哥都在南京读书。要是那个时我在成都,我一定知道更多的事情,我也会写得更详细、更具体。
我的三姐夫姓陈。我同他见面一共不到十次。他给我的印象,比我的一位堂姐夫给我的印象好。郑国光的作文中“我刘公川人也……我戴公黔人也……”这两句就是从我堂姐失的作文里借来的。他把作文送给他的岳父(我的二叔)批改。我在二叔的书房里见到这篇有趣的文章,到今天还记得那两句,就把它们写进《秋》里面了。我的姐夫好象一个文弱的书生,我的堂姐夫好象一个土财主。我把他们揉在一起成了郑国光。《春》里面的郑国光象我的堂姐夫,《秋》面的郑国光就是我的姐夫的写照了。我这位姐夫让我姐姐的棺材停在古庙里,连看也不去看一眼。他还找我大哥替他借了好几笔钱,不但不还,甚至避不见面。后来大哥终于设法把他请到我们家里去开过一次谈判。那个场面跟我在《秋》里描写的相差不太远。我当然没有参加谈判的机会。好几年以后我才听到那些详情,我就把它们写了下来。《秋》出版后第二年
我头一次回到成都,才听见人说,我那位姐夫的第三次结婚也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后来抽鸦片烟上了瘾,落魄地死在西康。
我的堂姐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他现在还在劳动改造中。这个人又象土财主,又象暴发户,一生靠剥削享福。他只懂得买田,田越买越多。他从不想用这种“不义之财”做一两件有益的事情。他不读书,不学技能。他花钱修了一所别墅,却不懂得如何布置房间。他需要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财产,却什么也生不出来,拼命讨小老婆,也没有一点影响。他每年过生日,想到自己无儿无女,没人接续香烟,一定要伤心地哭一场。他讨过几个小老婆,一个服毒自杀,一个跟人跑掉,最后的一个在他被捕以后也找到一位门当户对的丈夫另外结婚。听说他在劳动改造中倒学会了一种技能,所以期满出来大概可以独立生活了。
我在《家》和《春》里都提到陈克家父子共同欺负丫头的故事。这就是我的堂姐夫的胞兄和他们父亲的“德政”。当初,我的四姐还没有嫁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了这个故事。不过堂姐夫一家是成都南门的首富。他们有的是钱。我的二叔虽然熟读《春秋》,但是对于钱的看法,大概也未能免俗。所以他终于把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嫁给了那样的人家!接着我堂姐夫的那位胞兄又变做了我的表姐夫。我们亲戚中间对他们兄弟并无多大的好感。我们弟兄因为都喜欢那位表姐,对这门亲事的反感更大。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我们亲戚中间那样的人家常常成了羡慕的对象。既使人不可取,金钱却能通神。
从我上面的这一段话看来,淑英可能就是我那位堂姐。
其实论性格我的四姐完全不象淑英。在我的记忆中四姐好象是一个并不可爱的人。但是关于四姐婚姻的回忆帮助我想出来《春》的一部分的情节。从这里我创造出周伯涛这个人物,我也想出了高克明的另一面。既然做父亲的忍心把女儿到嫁到那种人家去,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忍心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一笔一笔地画出来周伯涛和高克明的面貌。这种旧世的父亲我看得多。不用说他们中间有的人面带慈祥的笑容。可是照我分析起来,他们不见得就比周伯涛或高克明慈祥。读者也看得出我写周伯涛时,心里充满憎恨。我恨这样的父亲,我愿意用我的笔来刺伤他。我常说我恨的是制度,不是人。但是这些人凭借制度来作恶。多少年轻、可爱的生命的毁灭都应由他们负责。我不能宽恕他们。
我在前面说过,淑英不是四姐。但淑英的父亲高克明却是我的二叔,也就是四姐的父亲。我这次修改《家》和《春》给高克明和陈克家两位都添上名律师的头衔,又把他两人的律师事务所放在同一个公馆里面。堂姐夫的父亲不是律师,他一生只做过一件陈克家大律师做过的事,那就是父子共同欺负一个丫头。有人说,他在分家的时候欺骗了自己的哥哥。那样的事冯乐山干得出来,我在补写的一章中已经提到过了。高克明做律师是他的本分。我的二叔就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事务所设在我们公馆里面。高克明在高家的地位和处境也就是二叔在我们李家的地位和处境。我五叔并没有把喜儿收过房。不过他和三叔都干过偷偷摸摸勾引老妈子的“风流”事情。他包了一个娼妓在外面租了小公馆。女人的名字是“礼拜六”,他还给她起了一个大号叫“芳纹”,我意外地在商业场后门见过“礼拜六”一面,她的相貌跟我在《春》里面描写的差不多。倘使没有“礼拜六”这个真名字,我纵有“天才”,也想不出“礼拜一”三个字来。倘使我没有遇见她一面,那么《春》里面淑英姊妹们也许就不会遇见她了。连五叔、五嫂吵架彼此相骂的话中也有一两句是他们当时驾过的真话。我把它们记在心里,并非为了日后好写小说。其实我并不要记住它们,可是它们自己印在我的心上了。大家庭中那些吵吵闹闹的琐碎事情,象克安同陈姨太吵嘴、觉群把刀丢进房里去砍弟弟等等都是真事。克明在那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我二叔扮演的角色。觉民因打觉群被王氏告到周氏同克明那里去,这也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还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扮演了觉民的角色,王氏应当改成我的五婶。五婶并不是淑贞的母亲,她一共生过三个男孩,活下来的就只有我的一个堂弟。五婶自己打肿了孩子的脸却要我来负责。我大哥起初希望我能够认错,后来又希望二叔能主持公道。他后来在二叔那里挨了骂,含着眼泪来到我的房间鸣咽地说:“四弟,你要发狠读书,给我们争一口气。”这个场面跟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完全一样。我大哥就是这样的人。他代我挨骂,我并不感激他。本来就用不着他跑到二叔那里去替我挨骂。他希望我扬名显亲,我那个时候就在打算将来有一天把李家的丑事公开出来,让大家丢脸。
不用说,觉新仍然是我大哥的写照。大哥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一个蕙,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蕙的影子。《家》的初版代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女人是一定有的,你曾经向我谈到你对她的灵的爱……”这是我的另一位表姐,她的相貌和性格跟蕙的完全不同。但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保留的表姐的印象和我大哥在去世前一年半对我谈起的“灵的爱”使我开始想到应当创造一个象蕙这样的少女。后来我才把三姐的事情加在蕙的身上。三姐的凄凉的死帮我我写成蕙的悲惨的结局。
海儿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小名叫庆斯。海儿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实情形写下来的。连“今天把你们吓倒了”这句话也是庆儿亲口对我说过的。祝医官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到今天我还仿佛看见那个胖大的法国医生把光着身子的庆儿捧在手里的情景,我还仿佛看见那个大花圈,和“嘉兴李国嘉之墓”七个大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嘉兴李国嘉”在《春》里面就变成了“金陵高海臣”了。
我二叔并没有象克明对待淑英那样地对待他的女儿。听说我的四姐出嫁后,二叔一个人在堂屋里对着他死去妻子的神主牌流过眼泪。我二叔中过举,在日本留过学,做过清朝的官,最后他又是有名的律师。他喜欢读《聊斋志异》,说菌松龄的文章有《左传》笔法,他为我同三哥讲解过一年的《春秋左传》。可是他会同意叫我的嫂嫂搬到城外去生产,叫他的小女儿缠脚。他续弦两次,头一位二婶我也许就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女儿都是第二个二婶生的。缠脚很可能是那位二婶的主意。我们小时候听见那个堂妹的哭声,看见她举步艰难的情形;大家都可怜这个小妹妹,因此也不满意她的父母。过了两年她的母亲死了。三叔又接了一位新的二婶来。我们都喜欢这位新的婶娘,她是一位忠厚老实、讲话不多的
年轻女人。缠脚的事似乎也就取消了。淑贞就是我那个堂妹的影子。但是我那位堂妹并没有受到父母的虐待,因此也并不曾投井自杀,象我在《秋》里面所描写的那样。然而我也想说,她并不曾受到父母的钟爱。我有这样的一个时印象:那个时候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做父母的人似乎就不懂得爱自己的儿女。孩子生下来就交给奶妈。母亲高兴时还抱一下,父亲向来是不抱孩子的,孩子稍微长大起来,父亲就得板起面孔教训他。对女儿父亲连话也不愿意多说。我的父亲在他的最后几年中间常常带我逛街看戏,那是非常特殊的事情。我的三叔惯用鞭子教育子弟,打得儿子看见他就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庆幸没有遇到这样一位严父,否则我今天也许不会在这里饶舌了。
我重读我的《激流三部曲》,我为自己的许多缺点感到惭愧。在我的这三部小说中到处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把克安丑化和简化也是《三部曲》中的一个小毛病。丑化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物。这个人既使在书中常常见面,也只是一些影子。这次我有意给克安添上几笔,我让他进克明的律师事务所给他的哥哥帮忙,我还写出他擅长书法,又点明他做过县官,在辛亥革命时逃回省城……这都是从我的三叔那里借来的。我的三叔虽然在外面玩小旦,搞女人,抽大烟,可是他写得一笔好气,又能诗能文,也熟悉法律,在二叔的事务所里还替当事人写过不少的上诉状子。人原来是复杂的。丑化和简化在作者虽然容易,却并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也应当说句老实话,我添的几笔并没有把克安写活。可见我并非真正的艺术家。 艺术家只消用简单的几笔就可以写活一个人。
在《春》里我还写了年轻人的活动。这也是我当时亲身经历国的事情。有人责备我把活动面写得很窄,有人责备我 没有写到工人运动。我设有话为自己辩护。我只能说,当时
我们这一群青年的活动范围窄,也没人来领导我们。觉民散发五一节传单的经验是我自己的经验。觉民在周报社的活动就是我自己的活动。不过我并没有参加演戏。张蕙如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现在还在成都担任学校的工作。方继舜的真名是袁诗尧。他编辑《学生潮》,为了梨园榜痛驾某名流的时候,还是高师的学生。他同我们在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我们都喜欢他。他后来加入共产党,在某中学当教员。在一九二八年的白色恐怖中他在成都被某军阀枪毙了。
我那些朋友当时的确演过《夜未央》。这是一个波兰人写的描写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三幕剧。一九○七年在巴黎公演,轰动一时,后来人有译成中文在法国出版。一九二○年有人在上海翻印了这个剧本。我当时看见报上的广告,用邮票代价买了一本来。朋友们见到它,就拿去抄了几份,作为排演的底本。在《春》里我本来不想多写《夜未央》的演出。其实描写淑英的成长和觉悟,不用《夜未央》的启发也未始不可。一九三八年年初我在孤岛上写《春》的后半部,当时日寇势力开始侵入租界,汉奸横行,爱国人士的头颅常常在电灯杆上,我想带给上海青年一点鼓舞和温暖,我想点燃她们的反抗的热情,激发他们的革命精神,所以特地添写了琴请淑英看《夜未央》的一章,详细地叙述了那个革命故把“向前进”的声音传达给我的读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为什么不给当时的青年指出一条更明显的路。我无法为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和错误掩饰。而且我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是写得太明显,也许书就不能送到弧岛青年的手中。
其实就是在三十年前我写下“春天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不曾料到“我们的”春天会来得这么快,并且在二十念候会有这样一个生产大跃进,革命干劲大发挥的空前的春天!
关于《春》我写了这么多的话。我觉得我也应当在结束了。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写一篇谈读《秋》的文章。今添还没有谈到的有些人和有些事情,我想留着在下一篇文章里详谈。
1958年1月27日在北京股票配资平台股票
发布于:北京市联丰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